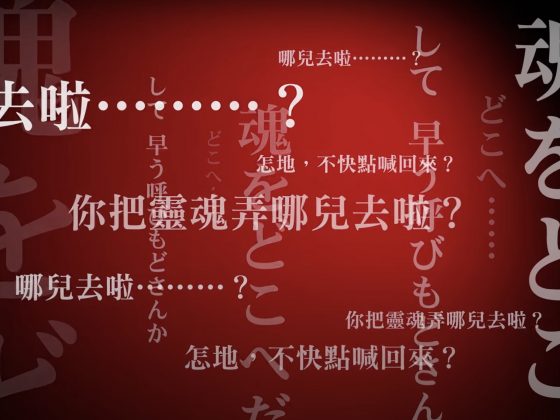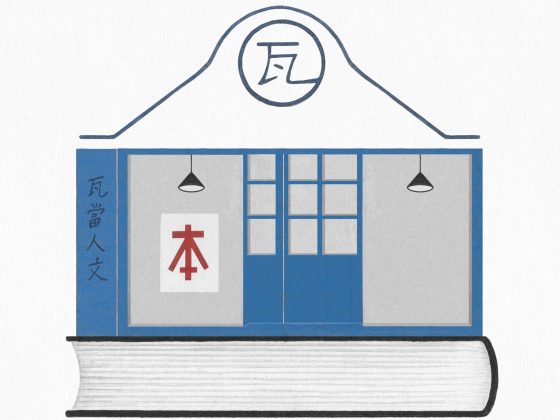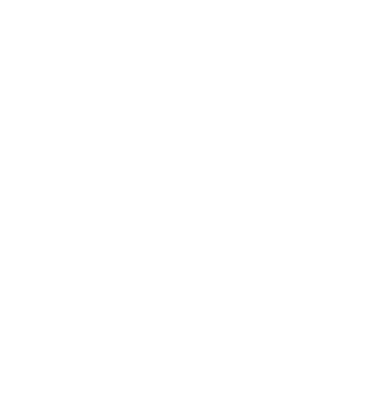書寫現實的詩人
接上了DREAM POP
關注內心 拋出對世界的疑問
《我們》
劉克襄|凹與山
我們 |劉克襄 我們是對的 上帝錯了 沒有人去過天國 去過天國的人都沒有回來 上帝是對的 世界錯了 我們棲息於死人遺棄的城市 忙盲茫漫地尋找自己 世界是對的 我們錯了 遠方的原野是殘存的快樂 那兒橫陳著未來 劉克襄 (1957~ ) 台灣自然書寫的先驅,直筆書寫現實的詩人凹與山Our Shame 以 Folktronica 貫穿,雜糅 ambient、downtempo,甚至受到 hip hop 影響的雜食二人組-凹與山(Our Shame),團名取用主唱小凹和鼓手 Isan 兩人綽號的諧音。透過鼓機、取樣機,把玩著電子聲響、木吉他質地、靈魂聲線,慶祝網路世代在現實人生遭遇的擦傷。
你覺得或相信,「一首詩歌,是不是可以改變世界嗎?」 「詩歌本身大概沒辦法。讀過某首詩歌的成千上萬的人,他們被詩歌暈染過後在日常生活中所累積的實踐大概可以。」--- 凹與山 第一眼讀到〈我們〉,就被用字的極簡力道和格式化的文字排列所吸引,有一種巨大而武斷的畫面感(上帝、世界、我們 / 對與錯、遺棄)。注意到作者是劉克襄老師的時候更是訝異,因為記憶中所讀過的老師的作品,是比較溫暖、自然寫實的,作品中充滿花草鳥獸的記敘,而非這種對仗工整、用詞灰心、控訴感強烈的氛圍。這樣的衝突感,更加深了我們對這首詩作的興趣。 延伸自這種「乍聽/乍看無法猜出作者是誰」的彩蛋感,我們在定調〈我們〉的曲風氛圍時,決定讓編曲的走向非常地 dream pop,一種凹與山從來沒做過的風格、聽感上離凹與山原本的電子都會感非常遙遠。(所以當劉克襄老師說,「成品和你們平常的歌真的聽起來很不一樣耶!」的時候,暗爽在心內) 與劉老師對談時,理解到〈我們〉的創作脈絡,發生在 1980、90 年代,整體社會氛圍有股對於全球化的經濟成長懷抱期待、同時卻有著成長焦慮,因此汲汲營營於拓建廠房商辦、歌頌都市化,卻犧牲了自然環境與棲息其中的動植物。詩人本身長期在媒體業工作、在淡水河流域進行生態觀察,且在那個年紀還有著革命青年的天真,所以寫下了這樣的文字。 凹山兩人出生的時期,其實已在詩人寫就這些文字的年代之後了,說是復刻這樣的情感實在不敬,畢竟我們並未親身經歷過詩人當下的感觸,因此我們改用「在天亮的時候,背著行囊去探勘城市廢墟」的感覺,重新建構這首歌的聽感。鼓聲希望營造出腳步的感覺,而吉他的音色則希望編織出一些天邊的金黃雲彩、silver lining 的色彩。 特別感謝這首歌的錄音及混音師,小林(聲波藝術),在製作過程中花了許多心思揣摩詞曲的畫面感,不藏私地端出復古盤帶,讓我們錄製電吉他時,能使用到原詩作誕生的年代的吉他音色。 不過,即便做成了我們原本不常見的曲風,還是希望加入自己原本喜愛的元素,例如:hip-hop(?),所以偷塞了一些銅管的聲音和 laidback 的鼓點(如果第二次副歌拿去當 hip hop beats 也不算違和)。 感謝夢田的邀請,讓我們毫無包袱地製作出一直嚮往卻從未嘗試過的曲風。仍時常想起深秋時,和劉老師一起在台北市最後的秘境 - 關渡大平原,欣賞金黃稻作和偶爾飛過的大冠鷲。 關於「我們」的10件小事: 1. 從台北市某個捷運站,出站走路10分鐘,你會看到一望無際的金黃稻田。 2. 大家聽到的明亮澄澈的顆粒感吉他,就像那時候看見的稻穗。 3. 請猜猜看是哪個捷運站(其實算是在某兩站中間)。以為來到嘉南平原,殊不知在台北市都會區。 4. 小時候在課本裡教大家賞鳥的劉克襄老師,等我們長大後真的親自帶我們去賞鳥(還看到大老鷹(老師:那個叫大冠鷲))。 5. 承上,老師那天被蜜蜂叮到(老師:那個叫馬頭蜂)。 6. 承上,那天是陰雨不斷的台北秋冬,少數陽光普照的幸運日。但小凹整趟旅程一直強忍噴嚏,因為小凹患有一種看到太陽會想打噴嚏的病(Autosomal Dominant Compelling Helio-Ophthalmic Outburst)。 7. 承上,這個病簡稱 ACHOO。就跟打噴嚏的聲音一樣。 8. 言歸正傳⋯⋯這是小凹寫過的歌裡,Isan 最快就會哼旋律的一首。 9. 下次演出,這首給 Isan 主唱,大家說好不好? 10. 不好。
沒有人去過天國
去過天國的人都沒有回來

遠方的原野是殘存的快樂
橫陳著未來
〈我們〉劉克襄|凹與山 - 公視:7/16 (六)下午4點 - 台視:7/16 (六) 下午4點57分 - Vidol、夢田影像YouTube :7/16 (六) 下午6點 - 三立都會台: 7/22(五) 晚上11點30半 - MTV: 7/24 (日)晚上9點 《我們》音樂聆聽連結